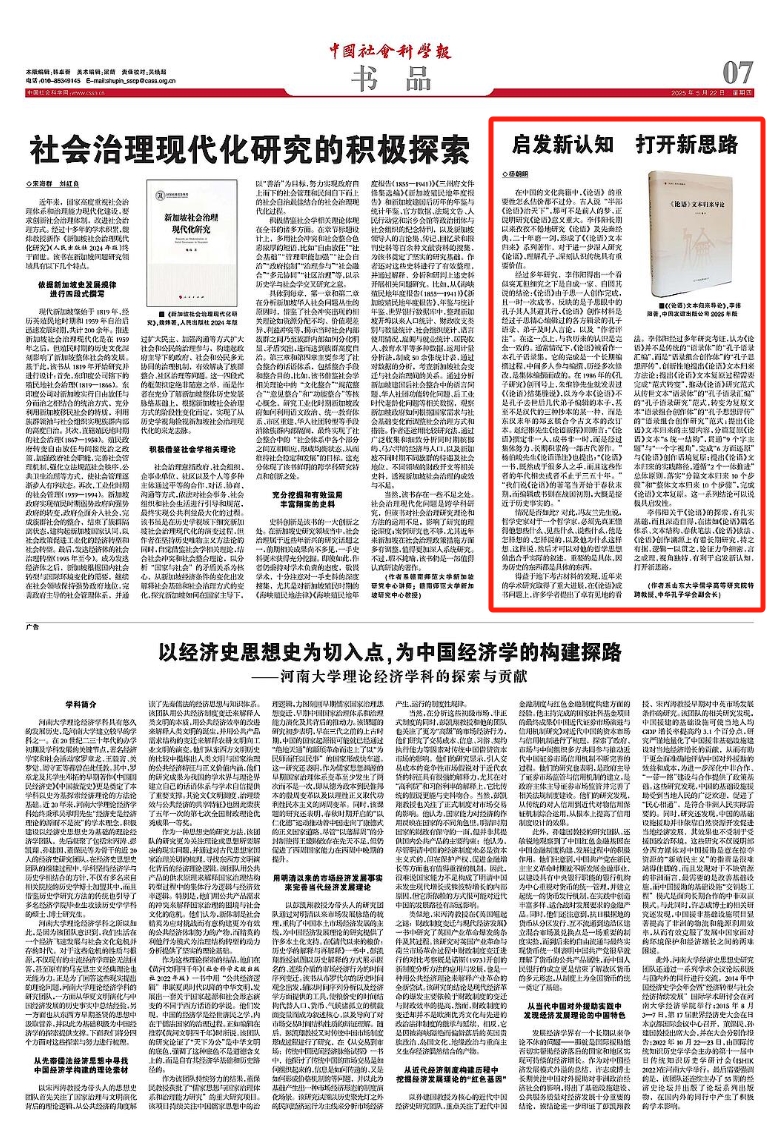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论语》的重要性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可不是前人的梦,正说明研究《论语》意义重大。李伟阳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研究《论语》及先秦经典,二十年磨一剑,形成了《〈论语〉文本归来》系列著作,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语》、理解孔子、深刻认识传统具有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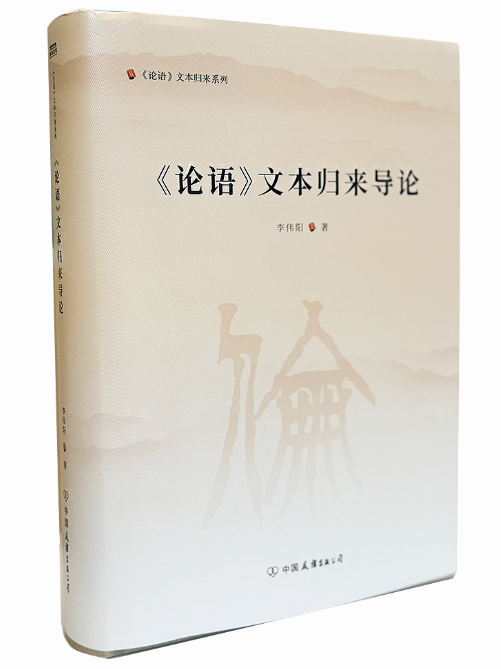
■《〈论语〉文本归来导论》,李伟阳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5年版
经过多年研究,李伟阳得出一个看似突兀但细究之下是自成一家、自圆其说的结论:《论语》由子思一人创作完成,且一时一次成书,反映的是子思眼中的孔子其人其道其行,《论语》创作材料是经过子思精心编辑过的各方辑录的孔子语录、弟子及时人言论,以及“作者评注”。在这一点上,与我历来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通常情况下,《论语》被看作一本孔子语录集,它的完成是一个长期编撰过程,中间多人参与编撰、历经多次修改,是集体编撰而成的。在1986年的《孔子研究》创刊号上,朱维铮先生就发表过《〈论语〉结集脞说》,以为今本《论语》不是孔子去世后几代弟子编辑的本子,甚至不是汉代的三种抄本的某一种,而是东汉末年的郑玄糅合今古文本的改订本。赵纪彬先生《论语新探》则断言:“《论语》撰定非一人,成书非一时,而是经过集体努力、长期积累的一部古代著作。”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也提出:“《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情况是否如此?对此,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史家对于一个哲学家,必须先真正懂得他想些什么、见些什么、说些什么,他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以及他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然后才可以对他的哲学思想做出合乎实际的叙述。重要的是具体,因为历史的东西都是具体的东西。
得益于地下考古材料的发现,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论语》成书问题上,许多学者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看法。李伟阳经过多年研究考证,认为《论语》并不是传统的“语录体”的“孔子语录汇编”,而是“语录组合创作体”的“孔子思想评传”,创新性地提出《论语》文本归来方法论;提出《论语》文本复原过程需要完成“范式转变”,推动《论语》研究范式从传世文本“语录体”的“孔子语录汇编”的“孔子语录研究”范式,转变为复原文本“语录组合创作体”的“孔子思想评传”的“语录组合创作研究”范式;提出《论语》文本归来的主要内容,分篇复原《论语》文本“6统一结构”,贯通“9个字主题”与“一个字视角”,完成“6方面还原”与《论语》创作语境复原;提出《论语》文本归来的实践路径,遵循“2个一体推进”总体原则,落实“分篇文本归来10个步骤”和“整体文本归来10个步骤”,完成《论语》文本复原。这一系列结论可以说极具启发性。
李伟阳关于《论语》的探索,有扎实基础,而且深造自得,在诸如《论语》篇名体系、文本结构、春秋笔法、《论语》读法、《论语》创作溯源上有着长期研究,持之有据,逻辑一以贯之,论证力争细密,言之成理,视角独特,有利于启发新认知,打开新思路。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