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有限的,平庸的成果就浪费了人生。所以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质量高,尽可能有创造性。”从事古籍整理编纂几十年,杜泽逊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高要求。
杜泽逊有着多重身份,比如大学教师、《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而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古典文献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投身于古籍的浩瀚海洋,他一忙就是一天,每天晚上十点多下班已是常态。61岁的他说:“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要敬业。我入了古籍整理这一行,就得干好它。”
偶然中的必然
1981年,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凸显,中文系以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孝纾为代表,称为“五岳”;历史系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为代表,合称“八马同槽”。杜泽逊正遇见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山东大学。“那时不仅能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先生的著作,有时会从年轻老师的议论中听到,甚至还能看到他们本人,听他们的学术讲座。”

上大学前,杜泽逊就对文学、古籍感兴趣。“我父亲是中小学语文老师,我经常看到他读书。”自小耳濡目染,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杜泽逊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献。萧涤非的《杜甫研究》,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黄云眉、童书业、高亨等先生的著作,杜泽逊都读过。“大学的时候不是全看,而是翻看,看序言,有的正文不一定能懂。”
大学期间每周日,杜泽逊会去逛书店。他最喜欢的书店在纬三路中山公园对面,叫古旧书店。书店的二楼是当时少见的开放性书架,可以随意挑书阅读,杜泽逊常常一看就是一天,店里的书几乎被他翻遍。
除了看,遇到经典著作也买。“那时在山东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7块5毛,我花了22块8毛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比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要多,买这一套书相当困难。”杜泽逊说。
杜泽逊走上研究古典文献的道路,其实有一定偶然性。经过大学四年的积累,他一开始定下的目标是报考当时山东大学文学院古汉语名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当年先生在全国招两个研究生,我一个同学跟殷先生平时学得多,我觉得竞争不过,这样还剩下一个名额,难度更大了。”于是,杜泽逊决定报考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古籍所1985年招了一个研究生班,一班10个人,而且古籍整理也需要懂古代汉语,懂文字、音韵、训诂,和我喜欢古典文献是一致的,所以就报考了,并且考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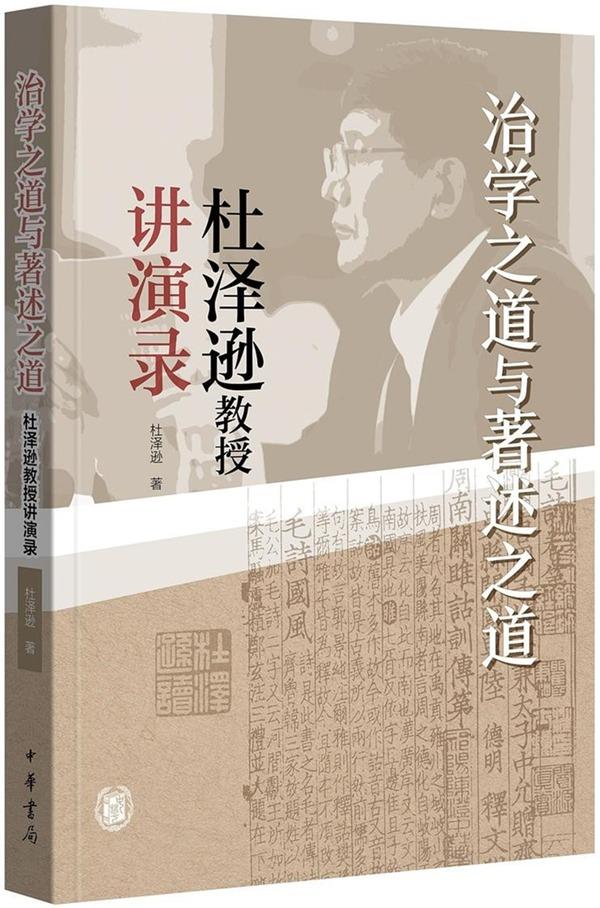
在古籍所学习时,杜泽逊常跟着老师读原典。“读原典不是讲概论,是领着你念,比如《诗经》《史记》。一方面多读了一些古书,另一方面加强了基础训练。”此外,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也成为他学习的重要内容。
毕业那年,杜泽逊得到了留校的机会,成为古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的助手。王绍曾的专长正是古典文献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1987年6月毕业后,杜泽逊在当年9月接到了第一项工作任务——带着《安徽文献书目》中的著作目录,去合肥找书,给这些著作分类。
这项工作其实是王绍曾当时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中的一项。北洋政府时期编纂的《清史稿》中,在《清史稿艺文志》部分分经史子集四类,给清朝人的著述列出了清单,但存在严重脱漏,为补齐清人著述目录,王绍曾主持开展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
到了合肥,杜泽逊每日都在看书。“我一次提几本书,看的时候要鉴定书写年代、作者的年代、书的基本内容,还要快看,100多部书大概看了小半个月,这也是一个挑战。”
对杜泽逊的表现,王绍曾在《文献学概要》序中写道:“泽逊在合肥留十余日,按图索骥,于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馆遍阅各书,详作札记,所有积疑,一旦涣然冰释。从此佐余纂《拾遗》,任副主编,夜以继日,无间寒暑者七载。”
致力名山事业不怕过程曲折
投身于古典文献学几十年,杜泽逊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古籍整理编纂项目。这些项目,几乎每一项都旷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杜泽逊告诉记者,他手头上现在有几个大项目齐头并进。到2024年,他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十二年;《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项目五年;《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三年;《山东文库·典籍篇》项目两年。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这些重大项目成果初现。
《清人著述总目》于2023年出了清样,由中华书局排版,16开精装40册,共25000页,其间参与的人员共计三四百人。“当年这些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现在都四十多岁了,散布在全国各地。我找到八十个当年参与项目的人,两人看一册,来完成校读清样的工作。”杜泽逊说。

“如果要给古书排队的话,《十三经注疏》应排第一,《二十四史》排第二。”杜泽逊说,“一套《十三经注疏》的木雕版,一万多个版面,有二三十个版本需要校对,每个版本要校对三遍。这样按页数算,《周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这3%的内容就要15个人校对一年。”要完成所有校对工作,只能靠团队。目前《周易》《尚书》《毛诗》已经完成校对工作,需要杜泽逊一字一句最后审定。
《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是杜泽逊手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他说,《永乐大典》具有资料性、工具性,其中引用的文本对研究者来说具有三个功能:找到已经失传的古籍;找到传世书的早期版本;找到分类的资料。“我们必须要采取拆书的办法,就像把原料按规划垒成房子,我们现在就是拆房,在拆的过程中就知道当年怎么黏合起来的,拆完后把砖、瓦、木头分类各自放,让它回归本来的元素。”按照计划,拆分完后,将形成《永乐大典》版本的《诗经》《史记》《周易》,等等。但由于《永乐大典》已大量消失,拆分出来的书籍并不全,比如《史记》130卷,只拆出了一两百条。杜泽逊说,目前第二步的拆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找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研究整理。
为了能随时掌握各个项目的进度,杜泽逊手机里的群聊一个又一个,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我的微信消息经常是一日百条,有些能简单回复‘行’‘是’,有的可能截了图,问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处置?我就要花点儿时间。”
在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杜泽逊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闷期。他参加的很多重大项目在考核中都是零分。按照规定,只有有了确切的出版成果,才能在考核中得分,而杜泽逊参加的重大项目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后才能出成果。这也意味着作为学校老师,杜泽逊在评职称、奖金待遇上要吃亏。“明知道要吃亏,我还是耐住性子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是这么考虑的,底线是不至于被开除,不开除我,不提职称、收入低点儿都没事。只要不开除,我就要坚持。”
青年学者在古典文献学上大有可为
自己坐过冷板凳,杜泽逊不希望青年学者继续吃亏。“现在的青年人在同一年龄段比我们这代人水平高,那为什么我们总是怕他们靠不住、坐不住?其实主要是因为考核。”杜泽逊说,现在各高校青年老师需要签预聘合同,几年一考核,有的学校还明确非升即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出很优秀的成果,每个学科情况不一样,有的学科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前沿,而有的学科周期偏长,其中就包括古典学科。
“古典学科周期偏长,因为需要熟悉很多文言文的原始文献和材料,理解起来难度大、消化过程长,进入创新阶段就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考核期限短,青年人就没办法坐下来、沉下心去学习,而是会追求短平快。就人才成长来说,违背了古典学科的研究规律。”杜泽逊说。

“古籍整理的人才就像打仗一样,要靠参加重大文化工程来成长,道路不通畅,谁还想参加呢?”杜泽逊告诉记者,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熬过沉闷期。而从青年个人来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的还是少数。
虽然面临的压力更大了,杜泽逊仍觉得当代青年学者在古典文献学上大有可为。首先是因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研究古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随着古籍的数字化、国际化,上网就能看到全国各地收藏的善本书图像。把这些丰富的古籍资源挂在网上,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国家图书馆一次上线上万部古籍,那得有多少页?是多么大的一个成果?过去我跑到合肥去图书馆一本本找书看,现在一个大硬盘就能顶一个小图书馆。”杜泽逊认为,现在青年人成才的硬件条件提升了无数倍,能在有限的人生中收集到足够的资料,一天能干前人一年甚至五年的工作,就等于延长了人生。由此来看,青年人超越前人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面对成倍放大的可能性,以及与之伴随的巨大压力,杜泽逊觉得青年学者还是要树立远大理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应对奋斗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青年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对眼前的曲折要以平常心态对待,要意识到眼前的困难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把曲折看成是非常态的,这是不正常的,这样就会容易太在乎眼前,觉得这个我一定要拿到手,就会容易焦虑,但是这个眼前往往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杜泽逊认为,加强理想教育对青年人来说很重要。理想教育并不是简单地描绘理想的美好,而是要认识到实现理想,是需要艰苦奋斗的。“其实这些在《二十四史》中都有,这就是以史为鉴。但现在很多理想教育还是空讲居多。当一个人遇到困难不会退缩,不会停止进步的时候,这个教育的目的就实现了。”
以开放的理念办好《文史哲》
今年,杜泽逊有了一个新身份——《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
自1951年创刊以来,《文史哲》始终恪守“学者办刊,造就学者”的原则。《文史哲》首任主编正是当时山东大学“八马同槽”中的杨向奎。而在杜泽逊之前的主编王学典,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
杜泽逊觉得,《文史哲》与科研项目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干项目,组织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本身是稳定的,也就相对封闭。而《文史哲》始终是开放的,定期公开,你发表了谁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哪个单位的?文章讨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一目了然。”

《文史哲》的编辑工作与古籍整理研究有着共通之处。杜泽逊告诉记者,《文史哲》从内容上偏向古文、古史、古哲,其中会引用大量古籍和文献资料。引用古籍的版本好坏会影响文章的准确度和学术品位。“我以前也做过《文史哲》的外审专家,对文献引用这方面是很留心的。”此外,因为《文史哲》包含的文章常涉及不同领域,需要在专家库中寻找合适的专家审稿,而杜泽逊在古籍整理过程中也需要与不同领域的专家打交道,在找专家这方面他有自己的心得。“《文史哲》是开放的平台,稿源开放,审稿专家开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思广益地把它办好。”
《文史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也是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被称为“学报之王”。这也让杜泽逊感觉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要把《文史哲》的高质量、高水平维持下去,就需要让人家把最前沿的成果拿过来,要持续不断地做这项工作,我的打算就是继续保持《文史哲》的特色,萧规曹随,率由旧章。”
《文史哲》获得学界赞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的传统。创刊之初,《文史哲》就有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的要求,也因此使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等等。对此,杜泽逊认为,扶植新人是《文史哲》的优良传统,在做法上就是不把年龄、地位,而是把稿件质量作为用稿与否的首要标准。“韩愈说‘闻道有先后’,他年龄比我小,但水平高,按韩愈的说法,就要‘从而师之’。《文史哲》用稿也是如此,只要成果是优秀的,不管年龄资历,该怎么录用就怎么录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事实上,《文史哲》的作者群已在迅速年轻化。杜泽逊认为,这展现出了《文史哲》与时俱进的一面。“我觉得中生代的青年专家很适合写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文章,我们作者队伍的年轻化也符合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梁雯)